溫任平:出書為防學術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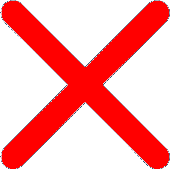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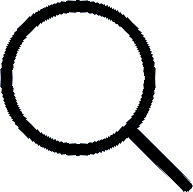
整理文稿,比寫稿還費力。早年的長短文章,都寫在標準稿紙,傳真給有關報章雜誌編輯處理。稿刊登出來,就剪下來留著,大多沒有剪貼,順手夾在圖畫紙的楬色檔案裡。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一直有這樣的迷思,以為自己有百藝防身,不會老,不會死,“年年十八,觀音菩薩”。詩人應該是長青樹,也因此這十多年來我全無出書的逼切感。
最近半年,發覺臉頰多了三小塊老人斑。驚嚇駭倒,漏夜扒讀有關幹細胞修復、道家修內丹,以及西方有關人類可以延年益壽的各種學說。折騰了一個多月,肯定自己搭不上“永生”的早班列車,乃全力寫稿、看稿、挖掘舊稿。希望快快多出幾部書,一旦我離開,在報章的紀念專輯上,寫紀念文章的朋友,至少還有些資料可以湊拼成文。
我在《南洋商報》“商余”版,寫過〈線裝情結〉,在“南洋文藝”還開過一個文學評論欄,欄的名稱已忘。我就是那么不認真,不知天高地厚。在《星洲日報》寫了多年的〈靜中聽雷〉專欄,一半出版成書,由吉隆坡大將書行印行。2003年4月6日之后的〈靜中聽雷〉,用心寫得文章不少,惜乎散佚在書房的幾個文檔,與〈線裝情結〉耳鬢廝磨,要把它們整理出來,太難太難。卓彤恩想幫忙,我說妳人在南京大學,遠水不能救近火啊。
在新加坡大學的某次研討會上碰見許通元,從他口中得悉,自己在各報發表的專欄文章,南方大學的馬華文學館都有收集。于是,我又放下心頭大石,要結集文稿出版成冊的決心也順便放下。
對整理文牘付梓畏之如虎
這當然不是許通元的錯。我搞文學評論,屬于有“文學史的意識”的人。在現實生活裡,我沒像已故李敖那樣,把資料分門別類,存在藥材店哪樣的百子櫃。我看書隨便亂放,讀書人的壞習氣,在我們身上體現無遺。我擔心這篇短文,到頭來會自爆我最能把書讀進腦去的地方不是在“秘方”(Secret Recipe),而是在可大可小的沖涼房,大家對我最后的一點浪漫聯想,遽而毀于一旦。
我喜歡大家把我想像成:把雙袖一甩,臉部微仰、右手卷讀《牡丹亭》的模樣,侃侃諤諤,莫非關馬鄭白、盧駱王楊。我酣醉于文學挑起的熱情與虛妄。有兩位文學同儕,直指我是魯迅與郁達夫的混合體,既關懷“國民性”(在我筆下是民族性),又無法完全擺脫精神的流放。我可以把一場文學演講,變成激情的政治演說;把政治演說,變成一次文學的抒情與敘述。我熱衷于跨界抑且乎“逾越”(transgressions),對整理文牘付梓的煩瑣零碎,畏之如虎,能躲則躲。
這大概可以說明,何以我自2004年出版詩集《戴著帽子思想》,即抱殘守缺(那些舊稿本)不出書、“不思進取”的原因。參與馬華文學研討會的學者專家,要找到我的文本作為研析的對象,的確有難度。也難怪某副教授根據我寫于高中時期的詩(收在1970年出版的第一本詩集《無絃琴》),判斷溫任平是個徹頭徹尾的浪漫主義者。16-17歲我不浪漫,肯定是賀爾蒙分泌失調。
我的詩作難找,造成的“學術意外”當然不止大馬留台學者一宗。有位留中的文學副教授,把淡靈的詩〈焚〉當作是我的詩,寫了篇《從“文體混血”比照陳瑞獻與溫任平的詩作》。我是廣東梅縣人,卻成了博士鴻文裡的潮州人,拜讀后不禁駭然失笑。
知道我再不出書,總有一天街招海報的標題、斷井廢垣的打油塗鴉、美容產品與政黨文宣,都可能成了我的“后現代詩”與“后殖民論述”,決定快快打包出版,不許延宕。噢,世界這么荒謬,真不想因為我的原故再多添幾分荒唐。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