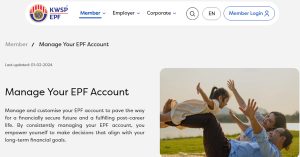溫任平:困難的過渡:漢語陌生化與英譯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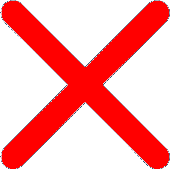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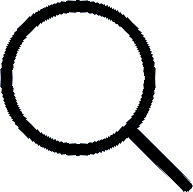
新的散文模式,大概在上個世紀90年代成形。據我的觀察,各種“后學”(postism)在80年代下半葉,開始進入兩岸三地的重要時段。六四學運對中國新一代文學復興的打擊,大概維持到1992年,我在1993年離開教育界,已經開始感覺到,大陸港台文字語言的變革,近乎刻意的、無所畏懼的革新。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就在關鍵性的1989年,天狼星詩社竟捲了鋪蓋,收檔走人。我們在相當程度上錯過了1986-1989年的文學知識與文化累積。我們錯過了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的教養與薰陶。
就在這時,台灣的文化研究風起雲湧,舉凡后殖民主義、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東方主義……在80年代下半葉幾乎侵佔了台灣從台北到台南的大專院校。80年代下半葉,90年代初,大家不怎么樣留意這些。倒是“三十而立”的警惕感,日益強化,社員先后湧入就業市場。市場發揮它的高度效應,把我們融冶成工作賺錢、生產消費的一環,只有很少人感覺有些什么東西變了,語言文字不一樣了。
我能追蹤到的文字變革出現在《亞洲周刊》,由邱立本擔任總編輯,與台灣國立大學外文系出版的《中外文學》月刊。《亞洲周刊》在1987創刊,即不斷試驗嶄新的報導語言,用的力度很大,讀者受益良多。1995-2005年該份周刊,其實已經成了我家裡的紙本華文老師。跨世紀的語言文字力求變化,配合新事物的出現,新概念的表述,令我這個老學生如沐春風。我一直以3年續訂的方式長期訂購上述月刊,沒有與當代漢語脫節。這是我個人學習生涯的大幸。
有些東西錯過就是錯過了
比較之下,我與《中外文學》月刊的關係嚴重滯后。那是我的不幸。大概在2004年我才聯絡當時在“華社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的潘永強博士,向中心外借15年的《中外文學》。換言之,我沒碰這份重要刊物長達15年或更久(1986-),落差巨大,仿似深淵懸崖,簽了名把書捧到車上的那一刻我痛哭失聲。我知道有些東西,錯過就是錯過了,可能窮盡一生也趕不上去。
90年代的《中外》編輯陣容幾乎每期都不同,胥視內容需要,由不同教授與研究生負責。裏頭有太多資料、資源,它的絕大部分論述都有強烈的英譯傾向,文字地雷遍佈。它的內容豐富:知識的、理論的、論述觀點的、論述策略的,十多年的脫節,我只能蝸步相隨。有些英譯中文,真的要費許多時間才啃得下。篇幅有限,這兒就不舉例了。
這個階段的大陸學術書籍,英譯的調門不怎么嗆人,但艱澀拗口,絕對不遜台灣。台灣的文學論述80-90年代嚴重西化,在90代末已漸改善,2000年以降《中外文學》提供不少良性西化的範本。大陸的論述,經常引錄二手翻譯,生硬無趣,有時真的猜不透作者想表達什么。大陸的著名學者汪暉,他的文化論著是讀不進去的“天書”。
經過這苦惱的過渡階段,我驚訝地發現有人如此議論沈從文不動聲息的砍頭書寫:“沈從文將傳統抒情文類的範疇,推至危險的極致,並藉此一展他前衛叛逆的企圖。”我更吃驚的讀到台灣總統選舉的時事評論,筆觸新穎、充滿創意:
“連迷稀疏,宋迷已老,當宋楚瑜站台叨念著《大宅門》連續劇的劇情和台詞時,馬英九卻成為年輕人心目中哈利波特的代言人之一。”
我乃恍然大悟:七、八十年代甚至90年代的散文好手,何以面對21世紀會“失語”“不知所措”,茫然不知如何去描繪今日的人情事理。他們緊抱住30年前的語言套件、詞彙組合,企圖為2015-2018年的時空留下印記,怎么可能?情懷已老,文字生銹,來來去去都是程咬金的三十六套,不管用。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