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才:帆布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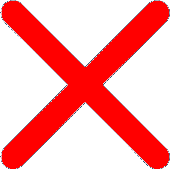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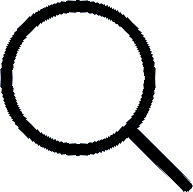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有人在面书张贴了帆布床照片,云:“谁还记得这是什么?”感触良多啊!直到9岁那年,我都是跟三姑睡同床。祖父去世后,祖母把中间他俩那睡房拆了,就与三姑睡在向街的头房。我们家是老店铺,因此厅子突然就变得很长很大,祖母买来三张帆布床,把四姑,五姑还有我,统统赶到厅子上去做厅长。从9岁那年睡起,姑姑一个个嫁出去,睡到21岁,搬离老店屋之前,我都是帆布床厅长。
三个少年人三张帆布床在大厅上还不是什么壮观的事,真正壮观的是在下面二楼。二楼共有24位金匠师傅,这些师傅都是南来的异乡客,全住在铺里,到夜里一床连一床,可从前面跳著帆布床跳到后面来。
师傅们的床阵,当时年纪小,一点不觉得怎样,但回想起来,他们只身南来谋生,白天埋头埋脑整个人紧紧凑著打金桌子,夜里摊开帆布床,就是客居他乡暂时能休息的一个长方形梦境了,那情景,还真有点像所谓的猪仔房。不过,情境很像罢了,师傅们不抽鸦片,我祖父做人也以厚道得名,师傅们生活稳定,夜里躺在床上闲聊、阅报或听收音机,有几个还拉起二胡唱粤曲。
听见南音我一动不动
睡帆布床,先就要学会如何扛床和开床。对9岁而且会在学校打架的我来说,一点不难。难的是洗床。帆布床当然要洗。不洗的后果,那就是每次经过二楼可以闻到那股老、中、青的男人“睡觉味”。他们也并非不愿意洗床,而是住在老店铺,洗床就得搬到楼下大街上去洗,每次至多只能洗两张床,这也难怪二楼长年累月都是男人味了。
17岁那年,姑姑都嫁了,楼上大厅只剩我睡帆布床,那么长的老店铺大厅;陈旧的木柱梁,烟熏的墙壁,剥落的灰水,空气中的霉气,仿佛就跟帆布床形成一个时代的绝配。有那么一回,我刚病好不久,放学后吃过午饭,就把帆布床扛出来休息,怎知昏昏沉沉睡到不清不楚,神志迷糊地醒来,大钟滴答滴答很清楚,四周已逐渐暗下去,大概祖母又到镜庄店搓麻将去了,大厅上一个人都没有,我只看到神桌上的油灯闪啊闪,一时间好像所有疑惑都涌上来,这时候更听到隔壁传来一阵幽幽的南音锦曲,老天,我第一次那么恐惧于还不会应付的孤独,躺在帆布床上,我变得一动不动,连坐起来,都不懂得。
我完全相信,每个时代里真有它自己特定的感受道具。对我而言,帆布床就是我那个孤独、苦涩又模糊的少年时代。后来,张爱玲写白流苏奔到母亲房里,向躺在一张昏暗大床上的母亲诉苦,但她完全感觉不到那个母亲是活著的,白流苏紧紧捏著手里做到一半的针线,连针扎进了肉都没有感觉——我,真的,这样的昏沉模糊,这样的孤独,无助,第一次就读懂了。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