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游自在◢少小清贫逆流上 儿戏扮老师 早慧明心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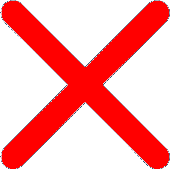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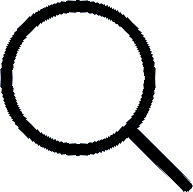
黄先炳博士打从小时候就把当老师的想望贯彻始终,小学热衷于玩老师角色扮演的游戏,初中已在课堂外的补习班教课,随后,一步一脚印走向正规执教路上,如今更兼负培育国内中文师资的使命,同时推动阅读教学,倡导儿童文学,把昔日童玩认真地过成生活大道。且来听一听这位2020年第33届林连玉精神奖得奖者忆述他逆流而上的来时路。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黄先炳博士在霹雳太平出世和长大,小时候家境清贫,“我们住的屋子类似七十二家房客,一家六口租了一间房,同一间屋子里,有五家住户,共廿三人同住一屋檐下。”
他说,其实,那是一间普通板屋,间隔成五间房间,分租给五个家庭,“居住环境相当拥挤,父母有张床,哥哥睡帆布床,我睡帆布床下面,两个姐姐则睡地铺床褥。”
“睡醒后,寝具都要折起,房间才腾出空间来用。”至于房间外,屋后空旷地是共用厨房,“每户人家拥有一个灶头、一个碗橱,还有一张饭桌,各做各的饭,各吃各的。”
印象中,厨房就好像小贩中心那样,“其实,整个居住环境相当热闹,也很方便。”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说,孩子都是一批一批一起长大的,“屋子前方,玩乐的人特别多。”
“童年生活算是多姿多采,大伙儿到河边游泳、抓打架鱼或豹虎,乐趣无穷。”至于家里的长辈,父亲一直跟着祖父打理洋货公司,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市区跟同乡一起干活。

慈母树立勤家榜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洋货店被超市击跨关闭,他无意间看到父亲月薪单据只有162令吉,家里的捉襟见肘了然于心。为此,两个姐姐升上中学后就辍学,哥哥则顺利完成大马教育文凭课程,“但是,哥哥考完试当天,就马上到北海工作了。”
“父亲白天在店里工作晚上才回家,所以,照顾孩子的责任落在母亲身上。”一直以来,母亲可说是撑起家里半边天的那个支柱。
“她平时会帮人洗熨衣服和床单,而我都会陪伴在侧帮忙她,尤其是工序特别麻烦的床单洗涤工作。我们必须先利用火水桶生柴火烧水,然后,再把床单放进去煮热。”
“同时,也把薯粉做成浆糊,煮热后的床单需浸泡在薯粉里头,之后才拿去晒太阳。床单会变得很硬,我们兄弟就会一人拉一角把床单扯开,以让它恢复成原来弹性。”
母亲就是用这个方法洗床单,他仍记得,每洗一张床单就会有四十仙收入。“所以,她会跟别人收很多很多的衣物来洗。”
“若是碰上需要熨烫的衣服,又要耗功夫做另一道工序,那就是昔日的熨斗都是放火炭的,母亲起了火,我就帮忙她扇火。”
只要碰到学校假期,母亲还会买些旧报纸回来,让他折成纸袋,“那时候,真的是用纸袋的哦!当时的纸袋分为两种形状,一种是三角形,另一种则是状如现在的塑料袋。”
“我们用浆糊粘好,然后,把纸袋卖给杂货店,以赚取微薄收入。”他说,在他成长那个年代,当地小孩赚外快帮补家用是普遍的事情。
“有些人会到附近的十八丁向渔民收虾只回来,然后帮忙剥虾壳,再转卖给酒楼。”这工作挺吸引人,但母亲不允许他们做,“因为长时间触碰到腥水,她担心对我们的双手不好。”
在他眼里,母亲是慈母,也是个严妈,“我们到外面去玩也得偷偷地,要是被妈妈发现的话,可能就会挨打了。但老实说,她也没有怎么打过我们。 ”
“有印象的一次是,当时下雨,我们偷偷跑到外面玩水,回家后便挨了数鞭。”由于居住环境人多口杂,母亲担心他们容易学坏,以致于对孩子的管教特别严格。
“尤其家里常常有人开赌,她不会阻止我们在旁边看人打牌,但我也不会参与,那是因为我怕被她责骂。”正因为这样,他才不像同龄朋友,长大后多半染上赌博陋习。
在严于律己律子的母亲身上,他看到一种勤家精神,“她是完全为了这个家而付出许多辛劳。”他有感而言道:“我们四兄弟姐妹都非常疼爱母亲。”

玩游戏丝毫不马虎
尽管生活清贫,居住环境也不理想,据黄先炳形容,他家的客厅有一两片天花板随时会掉下,屋子后方屋顶则在下雨时漏水,但他毫无怨言,也抱持正常心态面对生活。
他不会因为活在卑微之中而感觉卑微,“以今天的话语来说,理应就是用平常心看待,无需克服而是自然面对,我还经常邀请同学过来家里玩,他们也不会介意呀。”
言及于此,他才提到跟同学们经常动脑筋开发自个儿的游戏,当中,扮演老师角色是他最常也最爱玩的游戏,而他也直言不讳,自小就有要当老师的念头。
“不知为何,总感觉老师可以教人家读书和写字,这很好玩。”据他忆述,早在小学时期就开始好玩此游戏了,“妈妈又给我买了个小黑板。”他理所当然扮演起小老师来了。
“我把家里的木凳子拿出来给每个人当桌子,然后,让大家排排坐在地上,再拿起粉笔来在黑板上写东西。”他负责教导其他邻居的小朋友。
“也因为这样,我懂得的事情比他们多,从中学习不少。”不说不知,他甚至还会设计考题,让玩伴们考起试来呢。看来,他玩起这个游戏来丝毫不马虎。
除了教大家数学,他还教华文,“那个时期的家长,还是流行把孩子送往英校就读,以致于邻居很多都是英校生,包括我两个姐姐。”
“我就会教他们华文,教他们怎样认字、读字和写字,他们就是从我这里学到华语的。”直至大家都升上中学以后,这玩意儿就被搁置在童年时光里了。

初中即尝执教滋味
告别童玩的日子,不意味着黄先炳放下当老师的想望,初二那一年,他及早初尝执教鞭的滋味,“在偶然机会下,我接触到太平佛教会,开始在那边的学校科目补习班教数学。”
“我们的数学掌握得相当好,那是因为小学学过的内容,上到中学也学同样的,不过是换了一个语言罢了。”所以,他指出,就连练习本出现错误,他们都会帮忙修订。
在这个周末午后的补习班里,班上从小学到跟他同龄的初中同学皆有,“这是一项义务性质任务,虽然没有收入,但就是觉得好玩。”
回想这段陈年旧事,他笑得特别开心,“我们的时间特多,跟现在的孩子不一样。不过,幸好母亲都有督促我们温习功课,我常常在家里大声念书,念到全家人都听见才罢休。”
“当时心里已经有个想法,那就是长大后也要当老师,只是,从未想过当华文老师,因为很多字都不会写,老觉得自己的华文不见得好。”

中学时期,他已经开始留意报纸资讯,当时老师的底薪、顶薪,还有年度加薪,他迄今仍记得一清二楚,“当时就想说,如果大学毕业后去当老师的话,理应很不错(RM1060- RM2340)。”
这个单纯想法止于念头而未有行动,“未曾认真去想,也不曾仔细想过当老师的管道,还有需要念些什么课程,况且,附近邻居的孩子也没有人考得过大马教育文凭。”
哪怕是家中的哥哥,也是考完试后马上踏入社会讨生活了,而他,惟有在逆流中力争上游,完成中五再挺进中六,“很顺利地过关。”
他之所以用“顺利”两个字,那是因为当时对考试窍门一概不知,“不知道考试前需要什么准备,也不晓得如何专攻考试范围,这么一来,也就不会特地去应付考试了。”
1984年,他顺利以第一志愿考进马大中文系,“其他科系都不要,马大不要我,我就去台湾。”毕业后,中文系里的老师郑良树博士曾建议他攻读硕士,但他因家境不好,必须出来工作。
直至1996年,他以“儒学与小说:《三国演义》研究”之论文完成硕士学位,并于2005年成功考取中国南京大学博士学位。

一堂课大开眼界
当初对教华文缺乏自信的黄先炳为何后来主攻华文起来了呢?此时,他提到了上太平佛教会华文课后的一段人生小插曲,“当时,我上的是星期六傍晚的成人华文课。”
“那堂课让我大开眼界,它跟学校老师教的不一样。”他坦言,中学时上的华文课很沉闷,因为里头有很多古文,老师边在课堂上讲解,他们便拚命抄下白话文,过程感觉不到乐趣。
他在上述华文班有截然不同体验,“那个老师从天文地理乃至古今中外,总之什么都可以翻出来讲。”他说,老师的教材也很自由,这一刻讲元曲,下一刻可能聊韩愈的《马说》。
他继续说道,那位老师给学生自由选择篇章去阅读,然后印一张纸当讲义,“这样就可以上课了,那个当下,我才发现华文天地是如此广阔。”
“你知道那个老师是谁吗?”他突然有此一问,我一时答不上,他马上回说:“那是继程法师。”也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法师,也从此让他打开了一扇生命的门窗。
“我是如此幸运的,那一堂课后,法师就要到台湾受戒了。”这唯一一堂课却让他无法忘怀,往后的日子里,同学引导他去翻阅太平佛教会图书馆的书籍。
这馆内有历史、文学、佛教等不同内容书籍,“其实,这些书都是继程法师留下的。”同学们会按不同需要给他推荐书籍,于是,书越读越多,涉猎颇广。
他说道,有的书的程度甚至超越自己年龄层,好比: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年~1936年)的著作《西方的没落》,“那么硬的书,我也会去啃。”
至于那些中国唐诗宋词欣赏集,他也外借出去风雅一番,“家附近有个太平湖,拿着一本书,找个池畔,坐在那里翻阅。”他笑称,那是多么的写意呀!
继程法师启发他的因缘,他称之为播种哲学,“当老师真要有‘只问耕耘’的心态,不计较得失,因你不知道,有哪个人会因着你的一句话而受到影响。
“为与不为,差别很大。做了,可能有一天在地球某个角落会结果。”多年以后,自1991年彭亨州关丹德伦敦师范到今日的立卑东姑安潘阿富珊师范学院,他一直都在教华文。
这些年把昔日童玩认真过成生活大道的努力,也让他荣获2020年第33届林连玉精神奖,同一届得奖人包括:大同韩新学院创办人已故林景汉和加影华侨产业受托会主席已故吕兴。
不管在课堂里或是课堂外,他都把同个节奏融入到讲课中,以妙趣方式教汉语和中国文学,一生坎坷的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在他口中可成了豁达过活的“淡定哥”呐。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