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豪:被放逐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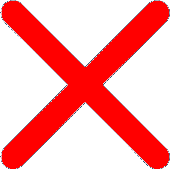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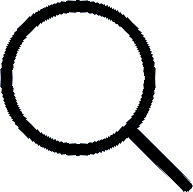
【理所当然的事情】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每次飞到香港小住,姑姑总会和我聊起父亲在海南岛加积参古岭村的生活故事。身为翁家的长孙,我很渴望多知道他们的事。父亲生前不多话,偶尔兴起也会讲些父亲和祖父祖母及四位姑姑破碎的生活片段。而我,拼命的把故事拼成一个画面,一个遥远又无能到达的地方。
父亲是翁家的长子,祖母再度连续生下了四个女儿。父亲成了家却与孩子无缘,当时在那片土地上,拥有儿子是面子问题。与堂兄说起土地的时候就处在弱方。当时父亲的堂兄这样得意的笑我的父亲:鱼活在池塘里,死了也是在池塘中。姑姑说,他的意思就是你没儿子,将来你的土地和其他一切也是归我这一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实。
后来父亲南来再娶,有了我们四个儿子。生活中,有些人还是抱着“理所当然”的心态。别人辛苦赚到的应该是属于他的,他的却就是自己的。这样的想法,不健康也不可理解。给是心意,不给是本份,都是我的权利。时代变了,现在这个环境已没什么“理所当然”一定和肯定的事情了。

【于是】

于是,我就在野花野草的微笑和喜悦之间,寻找到令我绘画生命的一种延伸。这样无尽的延伸是宽阔的,我的视野越来越有层次,美学趣味成了安静的空间。
那年我接触的先是西洋蓍草,后来又发现了野胡萝卜。两者属于黛西的家族成员,但就是野,没人理睬,没人疼惜。那年我们相遇在纽西兰南部的迪加宝村庄的草原,从此以后,缘起。
对于我,野花草美的浓度是深邃的,就因为这样深邃的美,需要从另外一个视角才读的到。这世上与时间竞赛的人太多了,有谁人会停下来望望这些不易读懂的美?我是野花的痴人,打从1990年后,我每年夏天都回到岛屿朝圣。只是为了与野花相处,我无悔。
野花美丽有其形象和视觉的特点,它们的特性从我的画作中缓缓渗透出来,一种平凡的坚定信念。我在它们生命辉煌的时候,用我的色彩、我的心意追求生命的质感。于是,我在它们生命的季节里进进退退。朋友说:“用你的色彩来提升它们的生命质感好像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说:“无论是人或是花草,有了爱的感觉,就有靠近就会有接触。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是一个被长辈忽略的孩子,我的自卑让我深深体会到一种被放逐的感觉。”在西洋蓍草和野胡萝卜的创作里,我读到自己。
【我的小时光】

一天到晚,我有许多小时光,清晨午后晚间的小时光,各有不一样的质量。一般来说,早晨是分享时光,与新朋老友一起分享早餐。午餐一般都自助,重点在于简单方便。小吃面包或是炒面条,一杯咖啡或奶茶,一天午后的时光启开了。
午后小时光是我的创作时间,我随心所欲地与颜色沟通,野花开了,石头成了形。石头上下叠着取暖,缝隙中有光透过,光影暧昧。穿越回去。野花并肩,斜侧的姿态最美。微风仿佛吹过,你听不到却见到摇摆的喜悦。
午后是我踏实的小时光,我停停画画,茶水少不少,有时有糕点,多是有饼干。走出工作室黄昏已至,晚餐时间到了。想要吃什么?就蒸金鲳鱼好了再烫一碟蕃薯叶,一人菜肴,足够了。一人独自吃饭也是很自在的,如果你懂得煮。煮熟之后随即用餐,省去等待省略时间,干脆俐落。
黄昏一杯奶茶几片饼干,这是我饭后的小习惯。偶尔也欣赏日落,七楼观赏日落,不须特地开车到丹戌河口,感觉有点奢侈。我喜欢小坐在书房看窗户外暮色渐渐转灰后沉淀入墨色。我这样的黄昏小时间,偶尔也有小改变,当我懒得下厨,我也会开车去一个小村吃阿参鱼,吃喜欢的tahu sumbat。简单的小时间,我的小生活。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