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任平:詩創作是語言的反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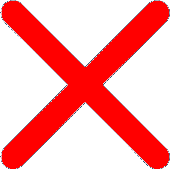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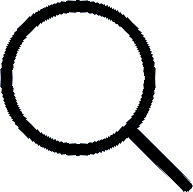
詩創作是一種反熵行動。所謂“熵”(entropy)是“能趨疲”,是信息的負值。語言文字在會議紀錄裡呆板癱瘓,在記者的新聞報導公式化的過程中麻木失能,只有文學(尤其是詩)可以把它喚醒,並且注入活力。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偶讀《老捨請吃糖瓜》,文章有趣。老捨,誕生于北京,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京派作家。老捨追述自己的一次“言語事件”。他去戲院后台看演員,剛好聽到下面的一段話:
“北京人習慣遛早,見面問個好,肚子吃飽,逛逛天橋。”
唱戲的楊星星順口就答:“天橋好啊!聽書、看戲、變戲法、吃不盡洋鼓洋號,曲藝大鼓蓮花落,爆肚、火鍋、扣肉、壇肉、燒羊肉、吃飽用不了兩毛。”
北京話語音色鏗鏘,猶如快板,落韻有力,親切自然,上面的對話都往好處說。好言悅耳是京腔的特色。
吆喝隱含音響碰撞
我特注意的是漢語的“活力因素”,語言是個生命體,樂音趨向使語言或婉轉、或諧和、或剛健、或雄渾。行酒令其實是唱酒令,少林武當練功的吆喝,也隱含敲擊的音響碰撞。
為什么搞音樂的一大票人,嚴重忽略語言的律動,文字組合的音色美聽?在我認識的詩人當中,林迎風是一個例外。迎風能譜曲,也寫了不少膾炙人口的歌詞,他的詩從來都不缺抑揚頓挫。我反而覺得他的詩太滑、太甜,需要一些“反說對撞”以凸顯某些矛盾與糾結。
毛譯東當年轉戰陜北,住進田家灣,主婦不安地叨念:“這窯洞太小了,這地方太小了,對不起首長了。”毛口裡喃喃說:“我們隊伍太多了,人馬太多了,對不起大嫂了。”這段話可非編造,而是毛澤東秘書的實錄。大家一定留意到毛與村婦語言模式的對應,這種對應自然而然的釋放出善意訊息。
可是只有文字的音樂性,詩仍無法存活。音樂性特強的打油詩,內容可能滑稽逗趣,文學的含金量卻稀薄。
詩需要一些思想內核,它的音樂性才有意義,語言美律才有寄寓。
透過詩學撼動人心
現代哲學向語言學靠攏,是維根斯坦(Wittgenstein)與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先后發現的趨勢,在詩裡,我們有話要說,那不是很自然的嗎?不一定是什么深邃的思想,只是一些觀察,一些尚未成形的思想點滴。總的來說,它們是廣義的知識。知識話語得通過生命話語才尋得出口。
什么是生命話語?當然是文學,尤其是對語言最敏感的詩。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都得透過詩學,才能有效傳遞知識,撼動人心,否則它們只是事實、史料、數據醃製的干糧。
中國30年代的救亡文學與口號詩,也算是思想美藝化的企圖。事過境遷,我們研讀30、40年代的那段歷史,可我們對那段日子的粗糙附生物:救亡與愛國文學已提不起興趣。
語言是生命體,它是生命動態平衡的一部分,從全息論(Holographic theory)的角度來看,部分正是整體的縮影。
清朝歷275年12帝,人口超過1000萬人,溥儀遜位不足半個世紀,大陸已沒有多少人懂得滿語、滿文。滿洲語文處于高熵,它的生命力消失得很快。語言沒有人使用,或本身的民族崇尚更高級的語文(比方說:英文),它面對的只有滅絕的命運。所有高階語文,都能用來寫出好詩。(2018/02/07)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